- 资质:
- 评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1分
- 印象:
- 经营时间:23年
- 展厅面积:
- 地 区:台湾-台湾地区
華建强個展 | 從繪畫開始
- 展览时间:2016-06-04 - 2016-06-26
- 展览城市:台湾-台湾地区
- 展览地点:也趣艺廊 | 台北市民族西路141号
- 策 展 人:秦雅君
- 参展人员:
展览介绍
從繪畫開始:與華建强2016個展
文 秦雅君
受邀參與這個展覽之前,我與華建强只有一次間接的遭遇。幾年前在我主編的藝術雜誌上曾經刊登過一篇推介其作品的報導,文章裡談了些什麼如今已不復記憶,只留下了「這個年輕畫家的作品還蠻特別」的印象。
就著這個幾乎不能算是認識的認識,我與華建强開始討論合作的可能。回應我希望能有更多藉以了解其創作的材料,他陸續提供了此前出版的三本畫冊,以及從上次個展之後累積至今約50幅新作的圖檔,除了以內容敘述其繪畫生產經歷過的變化之外,它們也以顯著的數量說明了作者曾持續投入的鉅量時間。就著這些進一步的認識,能否在從沒經驗過的「畫展」裡找到足以意味著什麼的參與位置,成為我毫不懷疑逕自投入的問答迴圈,直到獲悉華建强從沒打算要在這次的發表裡辦個畫展。
這個意外中斷了我原初的想像,卻也開啟了一個新的,伴隨著一個渴望認識的熱切情緒,一個對我而言終於開始意味著什麼的起點。
從繪畫開始
每每遭遇困局的時候華建强都會主動回想起自己差一點點就是個在高職畢業後做著並不喜歡的工作覺得未來沒有希望直到生命終結的人,如果不是自己主動改變了這個可能的話。
結束兵役後,華建强先後考進大學與研究所裡學美術,在這段期間,從基於好奇而嘗試交往的陌生對象,膠彩畫逐漸成為他最為熟悉與熟練的創作形式,這也使得他與藝術的關係開始於繪畫,一個相對資深因而有著諸多先輩的創造已積累成傳統的領域,然而華建强在其中所繼承到或許最好的一個是:要生產屬於自己的創造。
要生產屬於自己的創造,在一個擁有豐富歷史的領域中雖不是件容易的事卻也有著無數可能的取徑,華建强的第一步是試著回答研究所時期幾位老師的反覆質問――你的作品跟你有什麼關係?出自他的構想應用他的技巧並且由他親手繪製的那些作品當然不可能跟他毫無關係,於是這個提問顯然意味著其所要求的並非關係的存在與否而是關係的強烈程度,對此華建强給出的回應無論在概念上或形象上都有點卡通,其中最顯著的特徵便是在他的畫面裡出現了「我」。
引用了大學時期同學為他取的綽號,華建强發展出一個「老頭」[1]的形象讓自己成為作品中的主角,從此理所當然的在畫面上製播著自己的小日記,從自家陽台上放眼可即或每日慢跑時重複經歷的鄉野景致,到經常性發生極其一般的生活片段,以至透過不同媒介持續被傳遞的瑣碎事件……這些因為太過平凡因而鮮少被視為值得入畫的內容,如今不僅成為主要描寫的對象,同時還以色彩豐富瑰麗的材料與繁複冗長的製程被精心組構,是這雙重的引述使得那些「日常生活」開始散發出特異的光芒。
相較於合理的引進那些生活場景,無論是最初的「老頭」或是後來在出國駐村一類陌生環境裡的「小孩」,這些作者化身的出現或許有著更為深刻的意涵。他們以持續的在場告白著畫面中的一切源自並僅限於個人經驗,但弔詭的是眼前可見的一切其實無從連接到任何可能的生活場景,因為它們從來不是某個經驗的再現或變形,而是每一次對自身總體經驗進行重新提取與組構的行動,是性質迥異且從不曾相鄰的追憶在同一個平面上的一次次降臨,它們例證了源自並僅限於經驗的生產如何可能離開經驗最遠,以逼近創造誕生的時刻。
從繪畫開始
研究所期間及畢業後,透過各種獎項、展覽邀約及畫廊合作代理等經歷,華建强作為一個畫家的身份顯得越來越明確,每日投入相當的時間在住家兼工作室裡「上工」也成為他逐漸養成的固定作息,而在兩三年間累積了數十幅畫作的生產之後好好為它們辦個展覽似乎是一個最應該的安排,直到2010年之前他的確是這麼想的也這麼做了。
2010年8月,華建强於也趣藝廊推出個展「人奸仙境」,同時出版的同名畫冊裡收錄了所有尚未發表的平面作品,但展覽裡卻沒有。總共三個樓層的展場裡,少少幾幅畫作的比例明顯不如他為這個展覽所製作的「新作」,在如今僅能藉由作者回憶與展場照片所追溯的現場裡,雖然諸如雕塑、錄像、裝置乃至詩作等與繪畫迥異的外表是其最容易被辨識出的性質,但它們多數仍然與華建强的繪畫有著緊密的關連。
一樓是展示繪畫作品比例最高的一層,地面上鑲著人面的仙桃雕塑也有著與其膠彩畫相近的色澤、質感與形象。二樓以濕潤的泥土和小麥草在整個空間裡鋪設出數片人工「田野」,其間矗立著紅白相間的大型電塔,交織在空間裡的除了疏落有致的電線外,還有不斷從電線桿上的喇叭裡放送出的廣播聲,一個經常出現在其繪畫裡的局部配置在此成為環繞著觀眾的立體有聲場景。三樓裡有三件分別拍攝於巴黎和桂林駐村期間的錄像,前者的主角是在羅浮宮廣場上對著雕塑寫生的一個小男孩,印象裡出了畫面後他被爸爸賞了一巴掌,因為畫得不夠像;後者則是座落在大型公園裡的兩座戶外雕塑,在顯然從未移動拍攝位置的畫面裡看來就像是在時間裡幾乎無變化的一景,直到它泛起波紋的瞬間才得以被辨識出原來是映照在湖面上的倒影。
對於為何要在這次個展裡提出那麼多不同於繪畫的實踐,華建强無法給出一個決定性的因由,不過如果說離開既有的繪畫經驗正是「華氏」繪畫被生產的起點,那麼離開既有的繪畫形式或許是他早晚將尋獲的嶄新經驗。不同於從雕塑、錄像或空間裝置等領域開始並始終在其內部工作的創作者,雖然使用著這些異質媒介但華建强在作品裡所回應的依然是繪畫的問題。如果此前的那些繪畫是一種將諸多異質經驗凝縮於二度空間的行動,那麼在這個展覽裡他所嘗試的是同一種行動在異質空間的展開,一個從以空白畫布作為空白畫布移往以雕塑、錄像、空間甚至時間作為空白畫布的開始。
從繪畫開始
在歷經這段有些意外的回溯歷程後,我發現對華建强而言,作為一種毋須依賴特定時空的支撐即得以自我成立的形式,那些繪畫作品在被完成的同時已經俱足了在時空中獨自旅行的條件,這也是為什麼在一個擁有最大自主性的發表機會裡,他更寧願實現必須仰賴這個前提才得以實現的那些想像,一個以展覽作為空白畫布的開始。
因為應允加入這檔展覽扮演某種協力的角色,我得以成為一個近距離跟隨「這件作品」被逐步完成的觀眾,並在僅止於口頭表述或僅浮現局部的那些計畫裡持續遭遇吸引我對其萌生期待的屬性。
預計發生在一樓與二樓臨街面的是高度關連於其所在空間的兩個計畫,雖然在操作手法上都屬於對空間的重新布置,卻指向兩種不太一樣的空間問題。在一樓的展場裡,最顯著的行動是置入一組八人座的西式餐桌椅,然後在桌上很合理的陳設各式餐具以及在牆上很合理的掛上幾幅畫。展覽所在的也趣藝廊是一個以展售當代藝術為經營主軸的商業空間,從其鄰近多數已有些年代的建築群裡似乎看不出明顯的性格或趨向,雖然有著現代簡潔的外型但依然傾向低調的也趣在其間看起來並不張揚,門面上的大片落地窗扮演了對外櫥窗的功能,從多數展示著繪畫作品的畫面應可辨識出這是一家畫廊,那麼如果看到的是鋪著白色桌巾上面整齊排好成組食器與各種擺設的一張大餐桌呢?
透過一個曖昧化空間屬性的手勢華建强在這個場景裡同時想托出的是那些其實並不尋常的桌上擺設與繪畫內容,然而預計發生在二樓展場裡的卻是空間本身即為所有內容的一件。二樓展場臨街的那一側也有著大片玻璃窗,如果想要引進自然光線的話,在多數情況下明顯違和展場調性的那幅窗景有著期待觀者應自動將之忽略的理所當然,在對這個理所當然產生懷疑的情緒裡華建强決定邀請觀者轉身直面這片一直與所在空間並存的臨街景色,與此同時,在對空間的更動下這些視線將出於一個此前從不可能的位置。
一張小畫可以作為明信片直接寄給異國的友人嗎?如果可以它會經歷怎樣的旅程以及這些經歷又會以怎樣的方式被記錄下來?從一幅繪畫裡如何發展出一件錄像作品與一件立體雕塑?它們如何可能既各自獨立又在空間裡共同組構一個敘事?與前述的兩件空間性作品相同,在這個展覽裡的每一個實踐都離不開繪畫卻也都無法等同於繪畫,它們是從「如果還要畫的話可以畫什麼」逐漸往「繪畫是什麼」或「繪畫可以做什麼」的問題性擴充。
雖然有著大體上的規劃,但作為必須在展覽的現實化場景才足以完成的那些計畫各自在時間裡變化著,進而也使得由它們所構成的整體直到本文即將結束的此刻仍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一個活著的狀態。
每每遭遇困局的時候華建强都會主動回想起自己差一點點就是個在高職畢業後做著並不喜歡的工作覺得未來沒有希望直到生命終結的人,如果不是自己主動改變了這個可能的話。此時此刻我突然覺得這個展覽是個在性質上有點相似的行動,是一個從繪畫開始並且預期還會一直畫下去的藝術家主動投入的一場冒險,其賭注是在他的繪畫裡贖回一個仍足以流變的未來。

 庞明璇
庞明璇 未知
未知 张大千
张大千 马文甲
马文甲 李秀勤
李秀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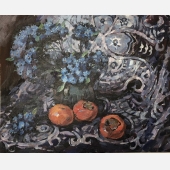 郭军
郭军 雷建华
雷建华 古巴塔
古巴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