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质:AGA 信 艺
- 评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6.9分
- 印象:
- 经营时间:43年
- 展厅面积:
- 地 区:北京-朝阳
镀金时代-叶永青的游走
- 展览时间:2015-12-05 - 2016-02-07
- 展览城市:北京-朝阳
- 展览地点:酒仙桥路2号大山子798艺术区
- 策 展 人:杭春晓
- 参展人员:
展览介绍
当“悖论”成为意义
——写于叶永青《镀金时代》之前
文/杭春晓
叶永青将展览命名为“镀金时代”,让展出作品具备了某种“文本”隐喻。但有趣的是:借用马克·吐温的文学概念,在他看来并非为了宏大的历史评判。他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资格评述一个时代。之所以用这个名词,是为了交待他描绘孔雀的背景:“一个镀满土豪金色的时代,整个夏天,我都往返于北京和大理画室里描绘和叙述着一个自闭的游戏——用几只孔雀来慢慢篡改窗外的世界。”
其实,我对他的“谦虚”深表怀疑。“镀金时代”与“镀满土豪金”的词语关联,和今天的生活太吻合了。即便,叶永青不想“评述”时代,选用这个词也是一种评述的态度。或许,这正是叶永青一代艺术家天然具备的创作倾向。不同于年轻一代,他们作品更容易在出发点上具备某种针对现实的介入性。然而,这个出发点并不影响叶永青作品在生产方式上具备另外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中愉快地达成共识。众所周知,叶永青是艺术界有名的“候鸟”——创作状态始终处于流动的过程。无论他选择“镀金时代”,还是其它什么主题,作品的被生产过程都具有相似发生。有人会疑问,这能说明什么?确实,按既定“创作——主题”的关系,无论作品创作方式如何,都服务于主题需要。也即作品自身的生产过程并不具备意义的表述能力。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叶永青一贯以来坚持的创作方式就是意义的生产过程。
正如我们在讨论中谈及的《富春山居图》,至正七年基本就完成了全画构成,但至正十年的题跋中黄公望仍然说没有完成,而将它带在身边随时添加。由于此后不久他即去世,没有其它题跋进一步说明画幅的完成状态。故而,以至正十年的题跋看,这幅中国绘画史的巨制是不是画完了,对画家而言可能还是个问题。然而,我们的阅读并没有这样的担心。我们总会以完成的预设看待一幅有着如此盛誉的画作——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一定是一幅完成了的作品。这种判断,隐藏了一种关于画作完成性的历史意识。于是,我们关于作品的判断,便与黄公望本人构成某种有趣的矛盾。当然,此处无意讨论两种看法孰对孰错,而是提醒我们,判断一件作品是不是也隐含了类似的意识,抑或说控制我们做出判断的文化权力?比如现在的工作室创作机制。是不是一件作品就应该在一个预设的空间内完成?谈及此处,我们会发现:叶永青“候鸟”式的创作,是将画作背后的时间流动加以显现,并因此检讨今天的作品生产机制。对叶永青而言,“候鸟”创作与其说是作品的完成过程,不如说是建立个体与作品的全新关系。普遍盛行的工作室中的画家与画作的关系,对叶永青而言难以忍受。他无法接受这种机制对个人的“囚禁”。在他看来,艺术应该凸显个体自由,如果艺术家与艺术品的关系被限定在某种框架内,艺术就不再具有价值。因此,他的“候鸟”并非简单的作品完成过程,而是一种态度——在自己与作品的关系中重新确立个体自由。
叶永青一直以来的创作,都有着类似的“机制检讨”逻辑。令人注目的“鸟”,就是针对他人“观看机制”的检讨:看上去简单、快捷的东西,却用非常慢、非常复杂的手段画成。如果只是认为“鸟”显现了新的美学形式,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叶永青创作的真实意图。他无意为世界多提供一种美学标本,而想通过绘画行为中隐含的“悖论”,揭示我们判断作品时的“认知机制”。就像《富春山居图》天然具有完整性不是作品本身带来的,而来自我们接受到的艺术史概念。叶永青的“鸟”看上去的“简单”,也是来自我们日常关于作品“简与繁”的理解机制。就此,叶永青作品的意义生产并不简单取决于“鸟”这样的主题,亦如今天的展览主题——镀金时代。行文至此,关于展览的描述早已偏离“主题”的存在。但为什么一定要一篇用以解释展览名称的前言?这里的某种规定性,亦如工作室机制一样,是今天作品生产、展示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一篇关于展览主题的解释文字,放在展厅中帮助观众理解。但在叶永青的这个展览中,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一篇文字来理解展览,那么你也一定会发现:这种“理解机制”正是问题之所在。因为看似合题的“孔雀展厅”后,你会面对一个看上去与展览主题毫无关系的展厅:一些原本散落在各个地方,或完成、或未完成,甚至还未动笔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4件一套的齐白石山水“临摹”。关于这套作品,叶永青说自己一时冲动决定创作后不久,就丧失了继续画下去的耐心。于是4件画作被“闲置”在不同城市,其中两幅还没有动过笔。但当这些作品被悬挂在展厅时,叶永青用现代展览制度制造了新的“悖论”:白盒子加video,让人自然地认为这就是完成的作品。这到底是不是完成的作品?从叶永青初始绘画经验看,答案是否定的;从现场观看制度看,答案是肯定的。两者间的“矛盾”,正是叶永青试图抛出的问题:一幅作品的意义是在工作室中完成的,还是在展厅中完成?甚至是在展厅之外继续“完成”?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溯自身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机制”。沿此前行,最终我们发现:叶永青无意提供什么标准答案,而是通过“悖论”促使我们进行一种“机制检讨”。显然“一件作品是不是完成了”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回答起来却要动用很多“隐藏在判断之后”的知识前提。从某种角度看,挑逗一些看似沉睡的知识前提,才是叶永青的真实意图。理解了这一点,自然就不再纠结于“一件作品是否完成了”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经过这一番思维检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展厅。此时,面对叶永青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布置,就无需诧异了。因为孔雀之后出现的未完成作品,正是针对今天展览机制的“悖论”制造,亦如其画鸟背后隐藏的“观看机制”的检讨。为什么展览需要一个提炼出的统一主题?这种习惯的背后是什么?显然,答案指向了某种文化制度中的权力机制。应该说,通过各种悖论制造,实现我们的思维转向——由“外在结果”转而检讨“内在预设的前提”,正是叶永青多年来坚持的创作方式。其意义不取决于那些看似结果的画作、展览,而源自这些结果产生方式的检讨。正如他的“鸟”,画面并非作品核心,这些画面调动起来的认识行为才是作品的真正发生。多年来,他仿佛一个超脱的“悖论魔术师”,通过候鸟迁徙、“随意”描绘等一系列艺术行为,不断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观念,并因此形成自己艺术方式的独特性,乃至本次展览关于“展览主题”的悖论制造。
走在这样一个展厅,我们仿佛进入“叶氏悖论”的多层“盗梦空间”。从“展览主题”到“作品完成性”、从“画幅生产空间”到“画家与画作关系”,甚至具体到一件作品的“简单”与“复杂”,叶永青为我们不断制造思维“悖论”。面临这些悖论,如果我们一意追寻标准答案,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叶永青”。因为,他的目的并非提供答案,而是为了一种思考机制的检讨。

 米振雄
米振雄 康蕾
康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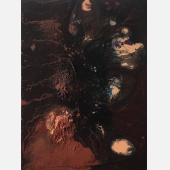 陆阳彬
陆阳彬 庞明璇
庞明璇 未知
未知 张大千
张大千 马文甲
马文甲 李秀勤
李秀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