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质:
- 评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7.1分
- 印象:
- 经营时间:25年
- 展厅面积:600平米
- 地 区:上海-闵行
汪建伟:骰子一掷 排演开始
2014-11-04 14:37:39
 艺术家汪建伟
编者按:2014年10月的北京还未完全褪去整个夏天残留下来的余温,五环外的黄港村已经因为11月的APEC会议被折腾的尘土飞扬一派工地景象了,艺术家汪建伟的工作室就位于这条常年被大货车来回碾压马路一侧,由于外面施工的声音嘈杂,工作室灰色的泛着铁锈的大门紧闭,如果不是大门上“W.J.W”的名字刻在上面,很有可能会被当做是和附近一样的民办小工厂匆匆路过。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艺术家汪建伟的助手已经前往纽约开始准备10月31日即将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的汪建伟个展《时间寺》,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也许鲜有人会有机会在那个著名的螺旋形美术馆里亲眼目睹整个展览。采访过程中汪建伟对于很多与自己作品密切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例如“潜能的时间”、“排练”、“形式化”、“普遍性”、“事件”、“去特殊性”“过度阐释”等等,这些关键词就像艺术家选择的线索不断将观者引入思想的迷宫,同时又迅速去破坏它,因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下一个“时间隧道”中继续“排演”。
艺术家汪建伟
编者按:2014年10月的北京还未完全褪去整个夏天残留下来的余温,五环外的黄港村已经因为11月的APEC会议被折腾的尘土飞扬一派工地景象了,艺术家汪建伟的工作室就位于这条常年被大货车来回碾压马路一侧,由于外面施工的声音嘈杂,工作室灰色的泛着铁锈的大门紧闭,如果不是大门上“W.J.W”的名字刻在上面,很有可能会被当做是和附近一样的民办小工厂匆匆路过。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艺术家汪建伟的助手已经前往纽约开始准备10月31日即将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的汪建伟个展《时间寺》,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也许鲜有人会有机会在那个著名的螺旋形美术馆里亲眼目睹整个展览。采访过程中汪建伟对于很多与自己作品密切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例如“潜能的时间”、“排练”、“形式化”、“普遍性”、“事件”、“去特殊性”“过度阐释”等等,这些关键词就像艺术家选择的线索不断将观者引入思想的迷宫,同时又迅速去破坏它,因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下一个“时间隧道”中继续“排演”。 “事件”本身包含很多的时间 关于“时间寺”这个概念,之前我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庙,这个庙你看到是12XX年建的,14XX年被烧,16XX年被盖了,18XX年又被拆了,你现在看这个进程,它就是一个庙,它不是五个庙,就是一个庙,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物”它是由很多“时间”组成的。 99艺术网:所以您这次在古根海姆的展览《时间寺》中的“寺”并不是一个地理位置和空间概念。 汪建伟:实际上很多“时间”构成了一个“寺”。而且这个东西分散在我们的知识和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中,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也许我们今天谈的福柯,他几十年前就死了,我们来谈本雅明,谈博尔赫斯,最后我们的行动,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一个时间里,但是我们最后不能做成若干个东西,最终就是做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包含了很多的时间,这个时间叫“当代”,就是它脱离了我们惯性的对时间的线性的认识,那就是说从昨天到前天、从前天到后天这是一种时间,要谈到时间观,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时间从来不是客观的世界,我们一直认为时间是什么,但是时间从来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时间永远是不纯粹的。在欧洲基督教的时间就是一个救赎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和统治,我们的时间观,实际上是基督教的时间观,从我们早期的教育直到现在的教育,可以说以前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现在叫“中国梦”,我们每一个对我们自己行动都是要在无限的积累当中才能到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救赎的,是基督教的时间观,不是客观的。第二,希腊的时间观是循环的,但是当代艺术的“时间”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不与今天的“共识”。所以说你做一个跟今天叫好的事情,那是“时髦”,我说的“不共识”实际上就是用今天的一个准确的时间来判断你的事物是不是有效,这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有效性恰恰是说明你不够“当代”,“时髦”首先是“当代”的敌人。 当代艺术的“形式化”就是“去特殊性” 99艺术网:现在会看到有些作品是在拼接时间,“错乱”是不是当代艺术其中的一个特质? 汪建伟:但是错乱最终要形成1,这个1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看到这个庙时并没有看见它拼接的痕迹,它只是由若干时间所产生的一个形式,这里必须要说的第二个东西就是“形式化”。什么是“形式化”?“形式化”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必须透明,“透明”是什么?“透明”就是没有“特殊性”,“形式化”就是你看福柯著作的时候,你不会先去了解到福柯是什么人,再回头理解他的思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去国外看展览,各种博览会、画廊展、双年展,我会首先被我眼前看到的这个“物”所打动,而且这个“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艺术家能够给一个完全没有了解他特殊性背景的人一次感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 你感动的这一瞬间根本不知道这个艺术家来自于何处,多大年纪,是男性、女性,还是黑人,假设你知道这个艺术家残疾多困难,你理解了他,但这个理解仅仅是在道德层面,主体是不在的,主体只是你的解释,多余的解释,这个是“缝合术”,把一个物缝合到另外的知识群,你通过另外的知识理解它了,这个“形式化”就不在了,这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中所认为的“内容高于形式”,所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幽灵”,我们总是要讲很多社会性故事、历史性故事,最终我们从来不对形式的单一性做出任何一个判断。你知道“形式化”里边包含了多少东西,所以说“形式化”就是它单一的思想行动,“排演”最终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后殖民的“多样性”是一个骗局 99艺术网:目前您的绘画、影像、表演是不是都在做一种“形式化”的尝试? 汪建伟:我说的“形式化”不是“形式”,“形式化”就是“普遍性”,从大的讲“当代”应该在当代条件下构成“普遍性”,我们读书,我们去看当代艺术,我们去思考社会,我们去看政治,我觉得“政治”应该包括当代政治里的创造性——阅读的创造性,艺术的创造性,在“当代”这个条件下和在“事件”层面上是共存的,这个就是我说的“普遍性”。简单地说这就是一种文明,就是规则大于特殊性。我觉得后殖民就是把这个东西偷梁换柱了,它看起来很尊重个性、尊重地区性,它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这叫“多样性”,但是“多样性”是一个骗局,这个世界的“多元性”才是一个真正的“普遍性”。 什么叫多元性?元与元之间是有“普遍性”的。“多样性”是只有一个元。我们说的后殖民就是“多样性”,到最后它的荒谬就展示出来了,也就是你怎么可能不是以一个中国地区的发言方式?所以非洲人最好是穿上羽毛,脸上有一些化妆,中国人最好是穿着中山装。现在很混乱,以前是长辫子和三寸金莲,后来又是毛的,现在有点乱,除了这三个以外怎么让中国人进入,这就是后殖民。“你怎么可能穿西服跟我们坐在这儿谈福柯呢,这不是你们要干的事。”这就是后殖民的荒谬,而且我们还把这个东西继承了,我们还说越民族的东西越伟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说我们接受一种歧视性条件,然后我们把这种歧视性条件当成了我们好像可以说话了,对不起,你除了介绍一下你吃炸酱面的经验没有别的话可以说。这个斗争实际上一直在进行,所以说这也是我在古根海姆展览中反“特殊性”的第一步。我就是艺术家,应该回到最普遍、最朴实的意义上来谈,请允许我不代表一个地区来发言,也请允许我甚至可以不代表某一种材料发言。 比集权社会可怕的是“自己”变成一个集权 99艺术网:就连卡塞尔文献展这种比较学术的展览在意识形态上似乎也避免不了对地区的划分。 汪建伟:关键是“地域”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多获利者。 99艺术网:汪老师您还说过“抵抗阐释”,为什么要反对? 汪建伟:这些东西都容易变成一种道德姿态,其实不是阐释,我觉得就看你能不能把阐释分解出来,其实一个人会说、会吃、会穿,会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把这些东西用一种很原始的,甚至我觉得是原始到家的一种现实主义连接起来,它可以有很多动力学联想,中国最可怕的就是动力学联想,什么事都可以联系,比如你今天说不喜欢吃辣的,这只是对眼前食物的一个判断,但是居然就可以联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有洁癖或这个人一定不喜欢做过激的行动。“他说他不喜欢吃辣的,所以画的东西很平静”这种动力学联想,可以把事情变得庸俗不堪。必须批判庸俗学联想,所以说拒绝阐释,这又包含了另外一个东西,结果反阐释就变成反知识、反任何可以超越个体经验的东西,所以最后人人都变成上帝了。有人就会说我不学习,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最牛B的就是我都是我自己。打个比方,有一天我的汽车收音机里有两个解说员在解说,一个说我们现在在谈怎么做回你自己,另一个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自己,所以要用自己的话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话去理解这个世界就变得很有意义。我到现在没明白这个“自己”是什么?除了我现在说的话,我现在使用的词,哪有自己的?任何一个人说是用自己的话说话,都是不对的,你是在继承一个人类的遗产。 首先我们今天的语言、表情,甚至所有表达思想的这种方法都不是你自己的,第二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不是,是你父母给你的,你的遗传基因里有80%甚至90%是父母给的。甚至包括疾病,哪怕是从生理学意义上来讲你都不可能有自己,所以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其实这是集权社会另外一个瘟疫,动不动就说我们反集权,我们要“自己”,实际上就是让任何“自己”变成一个集权,最后演变成集权主义,这就是集权社会更可怕的东西,任何人有一个集权的种子在自己手里,如果说我自己做主,怎么可能呢? 真正摆脱贫穷的方式是“平等” 99艺术网:其实这个“自己”还不知道是谁。 汪建伟:首先就没有这个概念,那为什么要相信这个概念呢?而且还把你所有的劳动交给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集权社会。所以说集权社会的日常化也是最可怕的,就是他把所有人都朝集权化发展。人要是有一个贫穷的逻辑,自然就会有变富裕的逻辑,所以我们战胜贫穷是为了富裕,但是这个逻辑是集权社会给你的。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中国梦”都包含了这个东西。所以,所有人都说要我们要富裕,就是因为我们摆脱了贫穷,其实真正摆脱贫穷的方式是“平等”不是“富裕”,贫穷最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是由于贫穷带来的“不平等”,所以说对贫穷最大的超越是“平等”,不是“富裕”。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贫困的,你就要变成了富裕的,这就是集权逻辑,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说你要做你那个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这个概念有的时候不是“平等”的概念,以“人民”这个概念说“人民需要权力”,这话的潜台词是比如说我在批评权力“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时候,突然发觉的是这个权力为什么不给我?因为你做得没有我好,我要做这个事情一定做得比你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候是对权力的渴望,而且不是对权力的蔑视,消解权力是为了要“平等”。 刚才我觉得用贫穷这个逻辑来说话,包括反对阐释,就出现了两个东西:第一,就是联想的动力,我们把阐释这个东西扩大了,但是人是需要的,就像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我喜欢吃辣的,这就是基本阐释,你说反对阐释连这个都取消了吗?其实是反对“过度”,“过度”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我们的一个阐释可以被无限度地引用在所有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说,我今天跟你说所有的话不能用于看我的作品,我用最原始的办法告诉你这个直接没有联系。比如,XXX在今天说天多蓝这句话就到此为止,不能用来看XXX说天是蓝的来分析她的爱情观,她的人生观、她的婚姻状况,甚至所有。 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阐释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个艺术家也许画了一张画有一块黄颜色就会引起无限度的联想,而且联想腐败在什么地方,全是已知世界的,我们掉进了已知世界的蛤蟆坑里,而且我们的批评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但是第二个逻辑又出来了,那好我们反对阐释就是你闭嘴,你说的东西你还看书,你还学术,我们就变成流氓,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我们是什么都不需要的。这就有了经常我会听见连一个娱乐界的媒体的主持人就要出来说做回你自己,我突然发觉这个“自己”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3D技术也没有达到这一步,就是做回自己。 “过度阐释”是一个社会形态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这样一种舆论背景下让艺术家很焦虑,就是媒体所宣扬的这样一种普遍给出的一种普遍经验,就是说艺术家都是属于有创造性的,直觉很厉害的,超于凡人的,艺术家也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描述,一旦艺术家觉得我要从别的地方像常人一样获得知识,就觉得很丢脸,就是说我死活要抵制跟常人一样的品德,我就是天生比他聪明,我就是不读书也会比你的知识获得量一样多,而且我就是说我的话就是我自己发明的,于是就有了一个更荒谬的词叫“原创”,它又被捏造出来了。艺术家都是原创,有的时候是被迫的,好象不承认这个身份就没有了,最后我说的过度阐释就是一个社会形态。 99艺术网:苏珊·桑塔格曾写过《反对阐释》这本书,她提到的感受力可能更强调一种回归。 汪建伟:苏珊·桑塔格说的那个东西太古典主义了,她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点道德的水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过时的。我们今天讲的反对过度阐释,实际上第一,刚才我说的“潜能”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矛盾体”的概念,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就是连这个都切除掉了,她让它不阐释,本身这里边放弃了我说的“矛盾体”的可能性;第二就是“形式化”这个东西被过度放大,只要有这个就会回到我们古老的另外一个逻辑上叫“眼见为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刀缝一样的界线,就是“看”包含了思和思想,但同时“眼见为实”又恰恰取消了这个东西,这个是非常谨慎的。所以应该少用警句、短句、概括去说复杂的事,比如说需要一百字、一千字说的东西就是需要长句去解释的,如果需要一句话就用不着说它一千句,这个就是“过度阐释”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东西。
编辑:丁晓洁
下一篇:国际拍卖行如何渗入中国市场

 测试艺术家
测试艺术家 卢延光
卢延光 雪山静岩博
雪山静岩博 马文甲
马文甲 李秀勤
李秀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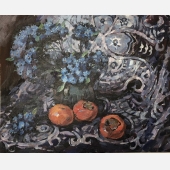 郭军
郭军 雷建华
雷建华 古巴塔
古巴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