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质:
- 评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8.3分
- 印象:
- 经营时间:16年
- 展厅面积:
- 地 区:北京-朝阳
与古接气,朴素驭法——马骏谈艺录
2013-02-19 12:18:01
编者按:仲春之末,莺啭花繁,日丽风清,神畅气宣。余携妻儿遊津门,造马骏,欢晤于其画室之内,静眺于彼海河之间。享天伦友谊之乐,品画图清言之闲。观其近作,叩其来源,闻其所赏,听其所思,不觉烦闷已远。骏于画史,取方晋玄;味冲神备,法接民间;离俗去障,素以为绚;融古道今,轻拨心弦。念世事纷扰无断,离体味画艺于无言,其中之谬,不亦间乎?归而有感,摘其俊语于后,缀吾闲话于前。子仁记。
与古接气,朴素驭法
马骏
一
在天津美院上学之前,我就开始喜欢玩那些古代的东西。当时我并没有古董的概念,玩起来也没什么标准。那时家里有不少老的美术刊物。我记得在封底或者封三、封二,总有一些青铜器、陶器什么的。刊物上偶尔介绍一些类似于发掘的东西,有的是黑白图片,但挺清楚,我很喜欢。那时我对残器并没有残缺的概念,一直到现在我也不太避讳玩残的东西。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味道完整就行,器物残了,但气比较完整,气息在,我就觉得好,能从很小的一个画面里解读很多东西。我玩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喜欢它背后的那段历史、它的审美,如果把背后那点背景、历史抛开的话,我觉得器物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
这两年,我不太喜欢怪异、出奇的东西了,更喜欢中正一点、平和一点的。这可能和自己的绘画审美有关系。我想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比较另类的东西,但是一件古代的艺术品如果能在一个比较大的审美范畴之内做一些“微调”,比如某些地方深一点,或浅一点,曲线直一点,或弯一点,就是在度上的调整,就比较好。这在有些人看来没什么区别,但如果自己去欣赏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微调是最大的变化。如果一件作品在大范畴当中能够做出一点精彩来,就特别对我的味口。汉俑里的侍卫抱着袖子往那一站,它在裙摆下面往里微微收一些,曲线的感觉就更足一些;另外一些可能直一点。那就看你喜欢哪一类了。
在我对古代艺术品的把玩中,我觉得它对我的最大帮助就是“接气”。东西上手的时候,是它的那种味道在吸引人,而不是这个器物或者残片本身。每个器物都像一本书,每个阶段、不同情境去解读它,看到的效果都不一样。
过去我对汉代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这段时间我忽然对北朝的东西感兴趣了,它有外来的审美,汉化的味道又比较重,像北魏、北齐这段,带点汉化,很鲜活,那种飘逸感、生涩感,和唐代的是两种味道,它的“放”是能“收”得住的。盛唐以后的那种放,我感觉有些撑不住,缺少“支撑”。所谓“支撑”就是审美当中起码的框架性的东西。每个时代再怎么变化,作品里那种内在的潜藏的度,它的要求还是有的,就是它骨子里的标准是存在的。历史上的工匠,他们的作品有工整一些的,有粗放一些的,但是无论怎么做,同一个时代的人手里的那种微妙手感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度,而且这个度很明确,是通过长年打磨形成的,非常精准,一出手就是下意识的。我认为就是这种下意识,对于现在的绘画来说是非常好的借鉴,要有一定的下意识。我们总说情感是一种流露,这不能说不对,但在艺术上更多的应该有一种很严谨的东西。当你情感到的时候,你的手感或是你的能量能够驾驭这种情感,而不是说情感到的时候你控制不住,流了,这就少了一份“支撑”,那份情感也就流失掉了。我觉得北朝的东西就是能够放得开的那种收,能收得住的一种放,是收放自如,非常好。这在同时期的石刻、陶器、石器上都能见到,大件也好,小件也好,哪怕就是一个杯子,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但是杯壁上的两条孤线非常有张力,深一点或浅一点,高一点或口沿往里收一点,都很好。
我认为民间美术是很细腻的。它的形式也许相对粗糙,但是味道是几代人打磨出来的,很细腻。过去我有一个汉代陶狗,是一个猎狗,就是很能跑、肚子高高的那种,头和身体都很简洁,但是它的肚皮那根线提得非常精准,成为整个陶狗最精彩的部分。当我仔细看它的肚子对缝线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很粗糙的刀痕,叠了至少两三层的刀,到位了,停了,刀痕还在,很粗糙,但很出彩。可是我看现在的工艺品,在表相上做了太多的东西,但它缺少的就是粗糙刀痕下细腻的、本质的东西。
二
这些年我的作品保持了一种延续性,没有太大的跳跃,只是我现在更注意神彩的把握,就是味道的纯厚度。这也像玩东西一样,在一种大范畴之内的微调。以前刚玩东西的时候,注意的是这东西“对不对”,当时“对”是一个标准,现在我觉得它就不是标准了,“美”才是标准。一个东西在对的基础上要美,要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特征,我认为这才是标准。在画面上也是这样,一幅作品首先是一张画,要把你心里的那种审美打磨得再精准一点。这些年我始终在做这种调整。
我不太去界定画中人物的身份,实际上它更多的只是我画面当中的一个形象符号而已。这种符号类似古代的高士——人们都这么说。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状态所导致的吧,比如朴素、安静,从内到外的安静。还有,这种形象对于我自身,驾驭起来没什么障碍;在我情感到的时候,用这种形象去传达这份情感,没有障碍。我不想给画上的形象附加太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年龄、身份,或是衣着,起码这些东西在我的画面当中并不重要。我比较关注的东西是形象在画面当中的位置,还有色彩、留白,点、线也是我关注的。
我觉得用笔始终是画面的骨。以前可能更注意的是线描、描法,还是停留在一个线上,现在同时还要强调造型,因为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形。笔墨问题实际上要落到形象的神采上。就像看器物,看到的首先不是器物本身,而是扑面而来的神采,是它的气息先打动人,之后才看到具体的制作方式。画画也是这样。我认为线条的质量、质感,一定要和人物自身的那种感情相融,浑然一体才好。例如宋代李公麟的线描人物,它高在让我们感觉不到线条的存在,尽管它是纯的线描,甚至他的绘画就是白描,不施颜色,没有色彩,但我们偏偏就感觉不到线的存在,而是一个浑然的整体。马蒂斯的绘画也让人感到是浑然一体,充满神采,其次我们才看到他们精准的用笔。如果抛开色彩、罩染这些问题,用白描独立成为画面,那么线条应该具备足够的表现力,才能够成为独立的画面,线条肯定要具备一些能量才能独立出来。所以线条里面的一系列问题,曲直的对比,转折弧度的对比,轻重的对比,要把语言都运用活了,鲜活化了,而不是简单地去描摹。再有就是用笔要落到造型上,位置很重要。在我来看,我更注重画面的切割,画面总是要有一条在主线层次上切割下来的一种矛盾的、对比的东西。在我的画面当中,我更喜欢这种。这段时间我又看了一些日本画,对色块、墨色、画面的分布这些东西,在意识上得到一些强化。
十年前我从日本绘画中学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比较生硬,但那时我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感觉眼前一亮,无论是色彩还是画面,和自己内心认识的东西非常贴切,只不过那时是把它割裂到自身画面之外去了。现在有一点比较好的在于,它能够成为我自身营养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这比以前有进步。其实凡是与此类似的,我都会有感觉,比如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受明代版画的影响,我的毕业创作画了一批《聊斋》的东西,都有明代版画的风格,包括我画的《水浒》插图。实际上我更喜欢比较整的东西,比如整块的色彩,甚至有时候我给画面只留一点白。我还注重边缘线。也许跟这有关系,我也喜欢欧洲中世纪的壁画和、高更、巴尔蒂斯、马蒂斯。实际上这类画家也借鉴了很多东方的东西,所以里面有一些产生共鸣的地方。
画面当中我不喜欢太张扬的东西,即便有也是画面的需要,我觉得能随时收回来很重要。作品中和人心里产生共鸣的东西,和人心里的力量合拍的东西,才是真正打动人的。
当一个画家在绘画上情感流露的时候,用笔爽快、率真,这是必要的。我的用笔比较急,行笔比较快,但是画面上还是需要安静,还没有做得太到位,至少这是我比较向往的。我总是认为画面过于技法化对我来说不是太合适。尽管我也从技法入手,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对情感流露或表现形成障碍,不够畅快就不好了。我觉得,一个画家对审美有一种流露的欲望,心底有足够要流露的东西,这时无论用什么样的笔法,什么样的方式去做,都是可以的。如果在画之前缺少一个支撑的东西,缺少一个你想捕捉的东西,便不太好。所以我认为下笔非常果断、不踌躇,是比较好的状态。
三
作为一个教师,我在教学中需要注意学生水平的层次差距。现在有的学生入学之前从来没摸过毛笔,这跟现在的考学忽略专业性有关,只重视素描、色彩、创作这些东西,不像我们上学时考小品画,考线描、写生,所以很多学生对于国画这种课比较陌生,尤其是刚入学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你的判断、你的敏感性,对学生的认知就很重要了。我一般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课上大量地穿插欣赏课,让他们先产生对绘画的向往,对审美的向往,而不是一上来就从技法切入,技法是放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当学生对一种审美产生想法的时候,他会主动去跟你勾通他是如何来完成的,是怎样形成这种手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技法最初是不存在的,什么十八描啊、皴啊、染啊,顾恺之当初也不知道自己的笔法是春蚕吐丝描啊,那都是情感所致,是在大的文化背景、大的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的绘画环境的产物,它和当时社会的文学、文化是统一的,不是脱节的东西,只是后来在人们的学习当中才总结出描法、皴法等等。所以我认为学习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学生的吸收过程、领悟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领悟能力确实要快,这个时候他对技法的把握能力也更快,从精神到手感上直接起作用。画画不是手的问题,不像弹钢琴,要手指长,画画更多的是你的这份情感,你的认知有多少。我的这种教法是从我在天津美院上学时就获得的,我做学生时起码有一部分老师是这么做的,我认为对我来说是特别受益的一件事。
现在能坐下来定定神儿仔细考虑、深究绘画,哪怕只关心一下自己的画,老实说这样的画家我觉得不是很多。也许人家也在想,但至少从画面上没有让人感觉到这一点。大家画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一些面貌了,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宝贝似的不肯放手——实际上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不过我觉得,安静地想一想还是很重要的。我始终觉得画画属于一个自己调整的过程,也许观众看到的可能还是一个画面,里面真正有多大动作,画家自己最清楚。也许你做得不成功,但是这份心思你要懂。我现在经常要坐在屋里去考虑,往前推好多年地想,最初为什么要这样?经常要回到最初那个点上,然后再绕一圈回来看看现在,经常要这样想一想。实际上有些东西如果不去考虑的话,有时候好像会失去一些氛围。我不相信,两个画家有完全相同的心境,或者有完全相同的手法。现在的绘画感觉不够真实,画家们考虑的东西不是太少,恰恰是太多,这个多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从画画的那天起,这就是非常自我、非常单纯的事,大家都在做着属于自己那块味道的事情,尽管这中间可能也有互相借鉴和影响,但是你自己从骨子里带来的那些东西要保留,自身有不足的地方要努力克服。好在我现在通过交往、交流,也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很多不足,特别是一些带有习气的东西。
有人说我不太注意观众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我的不足吧,审美上还需要再开阔一些。画家审美的开阔度,加上用笔的质量,决定了作品的厚重度。我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的还有书法,以及从宋元到明清以来那些比较系统的东西,就是一些前人梳理过的画论、经验。
对于绘画理论,我不是没有兴趣,但是的确看得不多。我感觉自己领悟到的东西和我后来读到的东西也有暗合之处。我现在的一些东西更多的还是自身对实物的判断,是从绘画本身理解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觉得以画论画还是不够,想在画外去开拓开拓,这样对绘画的把持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实际上对于传统的认知,我是不断反复的,不是直线的,总是不断重新再回去看一看,从一个点延续到另外一个点,中间有一个来回反复的过程,有时间上的跨越性,有时代上的跳跃性。就现在的关注来说,我始终还是喜欢在这几个点上,来回走得可能多一些。比如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尤其是那种风骨,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内心当中潜在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它是相连的。这也不是刻意,它和我自身对审美的把握、向往贴得更近一些。在心理上,在做事当中,在绘画上流露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由一些。在画面当中出现一些不经意的东西,随着一笔一笔的深入,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我比较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可能也是我比较迷恋那段历史的原因吧。后人对历史比较系统的回顾以及所做的大量文字工作,我对此是比较感性地去接触它。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对前人在审美上的发展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其中也有一些很新鲜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我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而不仅仅是从感性上去接触。
许多人在强调感受的时候却往往在乱来,那说明他们连“尊受”是什么还不知道,连起码的法都没有。一个中国画家不能一味地在那种率真和那种霸悍和无度上打转。其实任何一种形貌都有可能是率真的,而精细跟精道又是不一样的。
无论画法如何,画画内在应该具备的东西还是要保留的,我认为还是那个最朴素的东西,还是用那几个最朴素的语言,把它们发挥好。
与古接气,朴素驭法
马骏
一
在天津美院上学之前,我就开始喜欢玩那些古代的东西。当时我并没有古董的概念,玩起来也没什么标准。那时家里有不少老的美术刊物。我记得在封底或者封三、封二,总有一些青铜器、陶器什么的。刊物上偶尔介绍一些类似于发掘的东西,有的是黑白图片,但挺清楚,我很喜欢。那时我对残器并没有残缺的概念,一直到现在我也不太避讳玩残的东西。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味道完整就行,器物残了,但气比较完整,气息在,我就觉得好,能从很小的一个画面里解读很多东西。我玩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喜欢它背后的那段历史、它的审美,如果把背后那点背景、历史抛开的话,我觉得器物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
这两年,我不太喜欢怪异、出奇的东西了,更喜欢中正一点、平和一点的。这可能和自己的绘画审美有关系。我想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比较另类的东西,但是一件古代的艺术品如果能在一个比较大的审美范畴之内做一些“微调”,比如某些地方深一点,或浅一点,曲线直一点,或弯一点,就是在度上的调整,就比较好。这在有些人看来没什么区别,但如果自己去欣赏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微调是最大的变化。如果一件作品在大范畴当中能够做出一点精彩来,就特别对我的味口。汉俑里的侍卫抱着袖子往那一站,它在裙摆下面往里微微收一些,曲线的感觉就更足一些;另外一些可能直一点。那就看你喜欢哪一类了。
在我对古代艺术品的把玩中,我觉得它对我的最大帮助就是“接气”。东西上手的时候,是它的那种味道在吸引人,而不是这个器物或者残片本身。每个器物都像一本书,每个阶段、不同情境去解读它,看到的效果都不一样。
过去我对汉代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这段时间我忽然对北朝的东西感兴趣了,它有外来的审美,汉化的味道又比较重,像北魏、北齐这段,带点汉化,很鲜活,那种飘逸感、生涩感,和唐代的是两种味道,它的“放”是能“收”得住的。盛唐以后的那种放,我感觉有些撑不住,缺少“支撑”。所谓“支撑”就是审美当中起码的框架性的东西。每个时代再怎么变化,作品里那种内在的潜藏的度,它的要求还是有的,就是它骨子里的标准是存在的。历史上的工匠,他们的作品有工整一些的,有粗放一些的,但是无论怎么做,同一个时代的人手里的那种微妙手感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度,而且这个度很明确,是通过长年打磨形成的,非常精准,一出手就是下意识的。我认为就是这种下意识,对于现在的绘画来说是非常好的借鉴,要有一定的下意识。我们总说情感是一种流露,这不能说不对,但在艺术上更多的应该有一种很严谨的东西。当你情感到的时候,你的手感或是你的能量能够驾驭这种情感,而不是说情感到的时候你控制不住,流了,这就少了一份“支撑”,那份情感也就流失掉了。我觉得北朝的东西就是能够放得开的那种收,能收得住的一种放,是收放自如,非常好。这在同时期的石刻、陶器、石器上都能见到,大件也好,小件也好,哪怕就是一个杯子,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但是杯壁上的两条孤线非常有张力,深一点或浅一点,高一点或口沿往里收一点,都很好。
我认为民间美术是很细腻的。它的形式也许相对粗糙,但是味道是几代人打磨出来的,很细腻。过去我有一个汉代陶狗,是一个猎狗,就是很能跑、肚子高高的那种,头和身体都很简洁,但是它的肚皮那根线提得非常精准,成为整个陶狗最精彩的部分。当我仔细看它的肚子对缝线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很粗糙的刀痕,叠了至少两三层的刀,到位了,停了,刀痕还在,很粗糙,但很出彩。可是我看现在的工艺品,在表相上做了太多的东西,但它缺少的就是粗糙刀痕下细腻的、本质的东西。
二
这些年我的作品保持了一种延续性,没有太大的跳跃,只是我现在更注意神彩的把握,就是味道的纯厚度。这也像玩东西一样,在一种大范畴之内的微调。以前刚玩东西的时候,注意的是这东西“对不对”,当时“对”是一个标准,现在我觉得它就不是标准了,“美”才是标准。一个东西在对的基础上要美,要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特征,我认为这才是标准。在画面上也是这样,一幅作品首先是一张画,要把你心里的那种审美打磨得再精准一点。这些年我始终在做这种调整。
我不太去界定画中人物的身份,实际上它更多的只是我画面当中的一个形象符号而已。这种符号类似古代的高士——人们都这么说。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状态所导致的吧,比如朴素、安静,从内到外的安静。还有,这种形象对于我自身,驾驭起来没什么障碍;在我情感到的时候,用这种形象去传达这份情感,没有障碍。我不想给画上的形象附加太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年龄、身份,或是衣着,起码这些东西在我的画面当中并不重要。我比较关注的东西是形象在画面当中的位置,还有色彩、留白,点、线也是我关注的。
我觉得用笔始终是画面的骨。以前可能更注意的是线描、描法,还是停留在一个线上,现在同时还要强调造型,因为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形。笔墨问题实际上要落到形象的神采上。就像看器物,看到的首先不是器物本身,而是扑面而来的神采,是它的气息先打动人,之后才看到具体的制作方式。画画也是这样。我认为线条的质量、质感,一定要和人物自身的那种感情相融,浑然一体才好。例如宋代李公麟的线描人物,它高在让我们感觉不到线条的存在,尽管它是纯的线描,甚至他的绘画就是白描,不施颜色,没有色彩,但我们偏偏就感觉不到线的存在,而是一个浑然的整体。马蒂斯的绘画也让人感到是浑然一体,充满神采,其次我们才看到他们精准的用笔。如果抛开色彩、罩染这些问题,用白描独立成为画面,那么线条应该具备足够的表现力,才能够成为独立的画面,线条肯定要具备一些能量才能独立出来。所以线条里面的一系列问题,曲直的对比,转折弧度的对比,轻重的对比,要把语言都运用活了,鲜活化了,而不是简单地去描摹。再有就是用笔要落到造型上,位置很重要。在我来看,我更注重画面的切割,画面总是要有一条在主线层次上切割下来的一种矛盾的、对比的东西。在我的画面当中,我更喜欢这种。这段时间我又看了一些日本画,对色块、墨色、画面的分布这些东西,在意识上得到一些强化。
十年前我从日本绘画中学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比较生硬,但那时我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感觉眼前一亮,无论是色彩还是画面,和自己内心认识的东西非常贴切,只不过那时是把它割裂到自身画面之外去了。现在有一点比较好的在于,它能够成为我自身营养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这比以前有进步。其实凡是与此类似的,我都会有感觉,比如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受明代版画的影响,我的毕业创作画了一批《聊斋》的东西,都有明代版画的风格,包括我画的《水浒》插图。实际上我更喜欢比较整的东西,比如整块的色彩,甚至有时候我给画面只留一点白。我还注重边缘线。也许跟这有关系,我也喜欢欧洲中世纪的壁画和、高更、巴尔蒂斯、马蒂斯。实际上这类画家也借鉴了很多东方的东西,所以里面有一些产生共鸣的地方。
画面当中我不喜欢太张扬的东西,即便有也是画面的需要,我觉得能随时收回来很重要。作品中和人心里产生共鸣的东西,和人心里的力量合拍的东西,才是真正打动人的。
当一个画家在绘画上情感流露的时候,用笔爽快、率真,这是必要的。我的用笔比较急,行笔比较快,但是画面上还是需要安静,还没有做得太到位,至少这是我比较向往的。我总是认为画面过于技法化对我来说不是太合适。尽管我也从技法入手,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对情感流露或表现形成障碍,不够畅快就不好了。我觉得,一个画家对审美有一种流露的欲望,心底有足够要流露的东西,这时无论用什么样的笔法,什么样的方式去做,都是可以的。如果在画之前缺少一个支撑的东西,缺少一个你想捕捉的东西,便不太好。所以我认为下笔非常果断、不踌躇,是比较好的状态。
三
作为一个教师,我在教学中需要注意学生水平的层次差距。现在有的学生入学之前从来没摸过毛笔,这跟现在的考学忽略专业性有关,只重视素描、色彩、创作这些东西,不像我们上学时考小品画,考线描、写生,所以很多学生对于国画这种课比较陌生,尤其是刚入学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你的判断、你的敏感性,对学生的认知就很重要了。我一般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课上大量地穿插欣赏课,让他们先产生对绘画的向往,对审美的向往,而不是一上来就从技法切入,技法是放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当学生对一种审美产生想法的时候,他会主动去跟你勾通他是如何来完成的,是怎样形成这种手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技法最初是不存在的,什么十八描啊、皴啊、染啊,顾恺之当初也不知道自己的笔法是春蚕吐丝描啊,那都是情感所致,是在大的文化背景、大的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的绘画环境的产物,它和当时社会的文学、文化是统一的,不是脱节的东西,只是后来在人们的学习当中才总结出描法、皴法等等。所以我认为学习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学生的吸收过程、领悟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领悟能力确实要快,这个时候他对技法的把握能力也更快,从精神到手感上直接起作用。画画不是手的问题,不像弹钢琴,要手指长,画画更多的是你的这份情感,你的认知有多少。我的这种教法是从我在天津美院上学时就获得的,我做学生时起码有一部分老师是这么做的,我认为对我来说是特别受益的一件事。
现在能坐下来定定神儿仔细考虑、深究绘画,哪怕只关心一下自己的画,老实说这样的画家我觉得不是很多。也许人家也在想,但至少从画面上没有让人感觉到这一点。大家画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一些面貌了,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宝贝似的不肯放手——实际上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不过我觉得,安静地想一想还是很重要的。我始终觉得画画属于一个自己调整的过程,也许观众看到的可能还是一个画面,里面真正有多大动作,画家自己最清楚。也许你做得不成功,但是这份心思你要懂。我现在经常要坐在屋里去考虑,往前推好多年地想,最初为什么要这样?经常要回到最初那个点上,然后再绕一圈回来看看现在,经常要这样想一想。实际上有些东西如果不去考虑的话,有时候好像会失去一些氛围。我不相信,两个画家有完全相同的心境,或者有完全相同的手法。现在的绘画感觉不够真实,画家们考虑的东西不是太少,恰恰是太多,这个多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从画画的那天起,这就是非常自我、非常单纯的事,大家都在做着属于自己那块味道的事情,尽管这中间可能也有互相借鉴和影响,但是你自己从骨子里带来的那些东西要保留,自身有不足的地方要努力克服。好在我现在通过交往、交流,也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很多不足,特别是一些带有习气的东西。
有人说我不太注意观众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我的不足吧,审美上还需要再开阔一些。画家审美的开阔度,加上用笔的质量,决定了作品的厚重度。我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的还有书法,以及从宋元到明清以来那些比较系统的东西,就是一些前人梳理过的画论、经验。
对于绘画理论,我不是没有兴趣,但是的确看得不多。我感觉自己领悟到的东西和我后来读到的东西也有暗合之处。我现在的一些东西更多的还是自身对实物的判断,是从绘画本身理解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觉得以画论画还是不够,想在画外去开拓开拓,这样对绘画的把持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实际上对于传统的认知,我是不断反复的,不是直线的,总是不断重新再回去看一看,从一个点延续到另外一个点,中间有一个来回反复的过程,有时间上的跨越性,有时代上的跳跃性。就现在的关注来说,我始终还是喜欢在这几个点上,来回走得可能多一些。比如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尤其是那种风骨,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内心当中潜在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它是相连的。这也不是刻意,它和我自身对审美的把握、向往贴得更近一些。在心理上,在做事当中,在绘画上流露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由一些。在画面当中出现一些不经意的东西,随着一笔一笔的深入,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我比较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可能也是我比较迷恋那段历史的原因吧。后人对历史比较系统的回顾以及所做的大量文字工作,我对此是比较感性地去接触它。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对前人在审美上的发展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其中也有一些很新鲜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我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而不仅仅是从感性上去接触。
许多人在强调感受的时候却往往在乱来,那说明他们连“尊受”是什么还不知道,连起码的法都没有。一个中国画家不能一味地在那种率真和那种霸悍和无度上打转。其实任何一种形貌都有可能是率真的,而精细跟精道又是不一样的。
无论画法如何,画画内在应该具备的东西还是要保留的,我认为还是那个最朴素的东西,还是用那几个最朴素的语言,把它们发挥好。

 黄琦
黄琦 测试用艺术
测试用艺术 胡江
胡江 张明虎
张明虎 康有为
康有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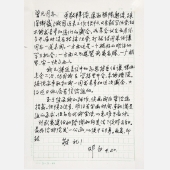 邓白
邓白 陈维廉
陈维廉 魏新
魏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