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善—七个为什么?
2014-04-16 16:09:31
七个为什么 于友善
随着在中国画这块园地里数十年的耙犁琢磨,时有收获,也时有疑惑。回想起来,早先阶段是收获多于疑惑,后半阶段则疑惑多于收获。这好理解,最初伊始,也就是大约十四、五岁时,我刚刚随师习画,那时候的收获可真是月月见长,接下来则是年年见长。那些岁月里,勤奋加气盛,外加当时(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对于绘画的要求以及评判标准也很单一、粗糙,自己觉得画艺疯长——无多时日,居然能把眼、鼻、口、耳描像了,勾起线来手不抖了,两下三下能够调出想要的颜色,甚至七拼八凑也能搭垒起一个创作的构图框架来了;而在这个阶段,疑惑困顿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再往后,尤其是进南艺读了本科及研究生之后,接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无意中发觉自己好像不会画画了;收获日渐减少不说,疑虑和困惑反倒不断的滋生:挺准确地画像一个人反被说成是造型不好、明明是用羊毫狼毫在生宣上分别勾出了干湿浓淡却被认为不会画国画、能够顺溜地数落出历代名家大师的姓名与代表作仍被看成是不懂绘画原理……到了后来,尤其是近几年,手头上和脑子里逐渐解决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自己似乎俨然实现了儿时想当画家的梦想,偶尔私下里比照前辈名家竟也暗暗窃喜。可一旦放眼外面的世界,又不免犯糊:是掉队了还是干脆就直接被甩出画画这个圈儿了?时常会受各式各样的困顿疑虑左袭右扰而难以排遣。这里的疑惑当然也有几种情形:纯属技艺与认识范畴的,还有观念与社会领域的。前者简单,技术层面和见解认知随着反复揣摩调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会有些许改观,当然,假如实在不行,怎么弄也无济于事的话,只能是听天由命——天生乏才也就认了,反正能应对工作应付画商,足已。而后者有所不同,那些统属观念与社会性的困惑则更让人煞费苦心也难以捉摸,这其中很多成分远超出通常意义的技艺与认知的层面。伴随这些疑虑困顿脑子里不由得生出些许的为什么来: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那样、为什么这个搞不懂、为什么那些不明白……
1关于大师 2关于怪画 3关于大展(评奖) 4关于评论 (标准) 5关于培养教育 6关于中西合流 7关于异域歧见
第一个为什么
记得刚刚改革开放那阵子,有俗言揶揄暴发户者:大街上被风刮倒一棵树,砸着十个人,其中有九个经理一个副经理。这本不好笑的笑话不多久应验到画界:九个经理变为九个“大师”,剩下那个是个“名家”。早先听闻某某大师、名家震耳发聩,肃然起敬。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这些高段位、高级别的姓名与他们的作品深入人心,犹如一座座大山矗立在那里,弥高仰止。将他们的名字串联起来镶嵌在整段中国美术史中,链接着前朝历代顶尖的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看着入眼,听着顺耳。回过头来看看周遭,漫天纷扬的“大师”“名家”名衔好像商铺甩卖似的毫不值钱,是个画画的都可分得一枚。这般情状,想必百姓与专家不免会犯糊,但让我犯晕的是,那些肩负头顶着赫赫炫目名衔的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倘若他们暗暗窃喜且抖惑发虚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揣着“大师”“名家”的衔头自认为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或许我们将此种现象理解为时代的呼唤和个人自身的祈求,便不难理解了。
第二个为什么
这年头走进画展,翻开画册,常常扑眼而来的是一些看不懂辨不清的玩意儿:不是些呆头呆脑、近乎残障就是呲牙咧嘴、狰狞滑稽的面目,再不就是几个不今不古的漂浮在亦真亦幻的场景里人显摆着令人费解的姿态和表情的人物。旁人看不懂倒也罢了,大半的作者自己也不一定搞得清怎么回事,而通常回应疑问则多半是一些本人说不清、别人也听不懂的支支吾吾。当然,话又说回来,之所以如此,在里面必定存在着某些顺理成章的缘由。纵观美术发展史,无论今古东西,各式各样的绘画样态,在其自身发展流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呈现出异于先前常态的模式或性状;任何画种的出现、演化、变革,都有其合理而必然的规律,中国画亦不例外。这犹如酵母引子在特定温湿度条件下逐渐催生、诱发面团扩散膨胀一般,一切所有的变化都有其前因与后果的自然关联。这里少不了内在和外界的各种因素之合力在共同起着作用;所谓内在因素,即是作者本人在从事绘画实践到了一定阶段,手头积攒与胸中储蓄累加集聚,酝酿膨胀到饱和的时辰,这时候的他,自然不满意原先的习惯模式,此时的眼界的提高和手上的变化,完全是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意图标新立异、惹人耳目之欲念在起作用)。而外界因素则更具催发性,古今中外那些适时而必然的革命性画风转换和潮流激荡,时时处处在影响、诱发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美术工作者们。面对今天这里刮了什么风、明天那里掀起什么潮,加之一些好事的以新潮引领者自居,煽风鼓噪、添油加料,再怎么有定性的人恐怕也难招架得住——不然的话,脱离大部队或者干脆被抛出圈儿外则显得很丢人。于是乎各色各样各类各型的招式花样百出,众人们整日介殚精竭虑挖空心思,不是琢磨个异腔怪调人模鬼样的就是打造个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标牌图式,弄些迷魂阵式的样态让人猜测也让自己迷糊。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类的东西能够让人记得牢,过目难忘。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很是有趣:在学校里呆了这么长时间,我发觉凡是那些绘画感觉与手头能力比较差劲的学生,往往容易走上这条路子;易上手、好操作,而且还能理直气壮地避开有难度、有深度的艺术理念与绘画语言方面的沟坎,假如再背诵上一些深奥僻涩的文字话语围遮拦挡一番,还真奏效。……
第三个为什么
自从董其昌发言“南北宗”,滥觞迄今,真搞不清利弊何属。翻来折去,到头来更多的是为那些实用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搬来挪去,做些自圆其说的辩解抑或颠倒黑白的谤言佐料。(可以断言,这如何也不是董老爷子的初衷)时常听闻某些显赫要人诟病江浙一带的水墨:游笔戏墨、俏薄油滑;又是单薄,又是轻浮……若是细审检索一番,江南这边的水墨画,确也存在笔力漂浮、形虚意散的滥竽之作。但此处他们所指并非于此,只要掉头回转扫一眼在他们眼里与此相反的比照物,便一目了然。看看那些所谓 “厚”、“重”、“沉”、“实”的水墨画(假如可以称之为水墨画的话)除了僵硬、死板,就是污糟糟、傻乎乎,
下一篇:于友善—南坡旧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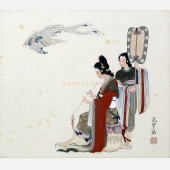 吴光宇
吴光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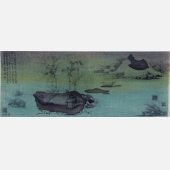 王霄
王霄 王轶琼
王轶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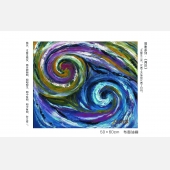 庞明璇
庞明璇 未知
未知 张大千
张大千 黄琦
黄琦 测试用艺术
测试用艺术
